全部文章

杨葵:看是进行时,看到是完成时
只是看就够了,别想着赶紧拍照定格,也别牵动向往回忆。如果不小心牵动了,提醒自己不要随之而去,立刻回到眼前,继续看
2024年01月01日 20:00


杨葵:重逢未必喜悦
很多重逢,乍看喜悦,深处可能是悲凉,是绝望。残酷的是,与人重逢常悲剧,倒是与物重逢大多是喜悦,是热烈
2023年11月07日 20:00


杨葵:物质丰富信息泛滥 生活中要勇于和善于删除
面对如今物质极大丰富、信息狂轰乱炸的时代,慢慢发现,生活中更需要像做编辑那样勇于和善于删除
2023年10月17日 20:00


杨葵:不时与旧事重逢,重读丰子恺《护生画集》
把自己和书桌都打理得明亮洁净,郑重翻开面前的校样,一幅幅护生画面奔来眼底,如静水深流,洗涤内心的片片污垢
2023年10月10日 20:00


杨葵:人处时间空间有潜意识默认值,单就审美而言趣味不同
如今年过半百,认清自己,就得独辟蹊径,寻找既适合自己趣味,又不过分挑战自己人性弱点的方法
2023年08月25日 20:00


杨葵:一个人真有正常不正常之分吗
种种缠绕像线团无法择出线头来,但是你老想把线头找出来重新缠一下。真有正常不正常之分吗?线团真有个头可寻吗?不如直接一刀挥断
2023年08月18日 20:00


杨葵:江南雨季
亲历太多东边日出西边雨,一秒钟前还响晴薄日,霎时间就大雨倾盆,就明白了什么叫小气候——雨线时常就在眼面前儿,晴雨就在一线间
2023年08月11日 20:00


杨葵:假大空悄然返场,大处无以论只说文艺
一不留神儿,假大空同学去爪哇国度了个假,悄然返场了,装扮华丽时尚,定睛瞧瞧,汤换了,却还是那包药
2023年07月12日 20:00


杨葵:文化制约人类,什么制约文化?
随着人类早期文化的发展,逐渐形成了一些框架,而后纵横交错叠加,越来越定型为一组复合型的、相对固化的框架,且越来越坚固
2023年06月27日 20:00


杨葵:学书法也好,学茶道也罢,一切尽在似与不似间
学书法也好,学茶道也罢,陷在技术里不能自拔不可取,不拿技术当回事,虚妄求道也不可取,一切尽在似与不似间
2023年05月12日 20:00


杨葵:流逝的不是时间,而是我们
“人从桥上过,桥流水不流。”我们迈过生老病死一座又一座桥,桥边花开花落,桥下流水不腐
2023年03月29日 20:00


杨葵:新年三愿
一愿来年勤于劳动,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;二愿来年少看屏幕,包括电脑电视尤其是手机;三愿来年多做实事,少看少听少写,更少说
2023年02月14日 20:00


杨葵:山居之后
住在山里,听觉、视觉、嗅觉都会越来越灵光,你会有点惭愧——原来我们的身体器官这么厉害,以前一大半都没用到呢
2023年01月30日 20:00


杨葵:搬家琐屑
终于决心彻底搬家。那些书跟了我这么多年,早已是我生命的一部分,想必和我一样,在每一个静夜轻声呢喃:不如归,不如归
2022年12月19日 20:00


杨葵:离别无处不在
曾经听一位智者说,通过努力实践,他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了一种习惯,随时与万事万物告别。因为每一次再见,都有可能是此生的永别
2022年11月04日 20:00


杨葵:放弃内外之分
《左传》让我着迷的地方,是那些简洁字句背后当年人的用心。语文层面,字词越来越多;叙事层面,层层加码。我看到人心越来越复杂、琐碎
2022年09月09日 20:00


杨葵:追问一句“然后呢”
说效率,说专注,好像都是在说戒。追问一句“然后呢”,就会发现戒只是手段,再往前走一步是定。再继续追问“然后呢”,答案就是慧
2022年08月13日 20: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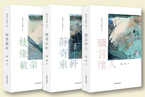
杨葵:常识、逻辑和爱,看似简单却是最难
太阳底下并无新事,孔子当年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,今天人的心里变幻莫测,穷追到底也无非那些旧情感、旧道理
2022年07月20日 20:00


杨葵:把默认值调整到自我反省
提醒别人“正确”使用“的地得”的人,可能很多还都保有21岁的生猛,还都保有若干奢望,还没被生活缓慢锤过
2022年06月01日 20:00


杨葵:楷定作品层次,我的书法“四法印”
如今各种因缘,重拾笔墨纸砚抄经、临帖、写字。如同少小离家老大回,再见亲人,表面没多热烈,心底却是认回了亲人,从此安分过日子
2022年05月14日 20:00

加载更多

杨葵
作家、出版人,著有《在黑夜抽筋成长》等书。
专栏最新文章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