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般来说,寿命越长,越有机会把握话语权。照此逻辑,当事人的口述,通常被视为一手研究史料。“圣约翰大学的专业跟今天不一样,圣约翰大学本部只分文科、理科,医科在另外一个地方,我们不大碰头”(周有光 马国川 《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》载《读书》2010年第10期)。
但这一次,周有光先生的自述有偏差。当然,也无必要苛求百岁老人的回忆细节。作为文科生,周老当年恐怕并无机会了解医学院的课程安排。事实上,圣约翰医学院的人体解剖教学现场,就设在梵皇渡校园的格致楼(图一)。这栋经社会募集3万美元,花费一年时间修建的崭新大楼,各层分别安置了化学、物理和医学专门教室。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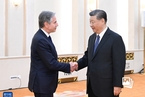


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